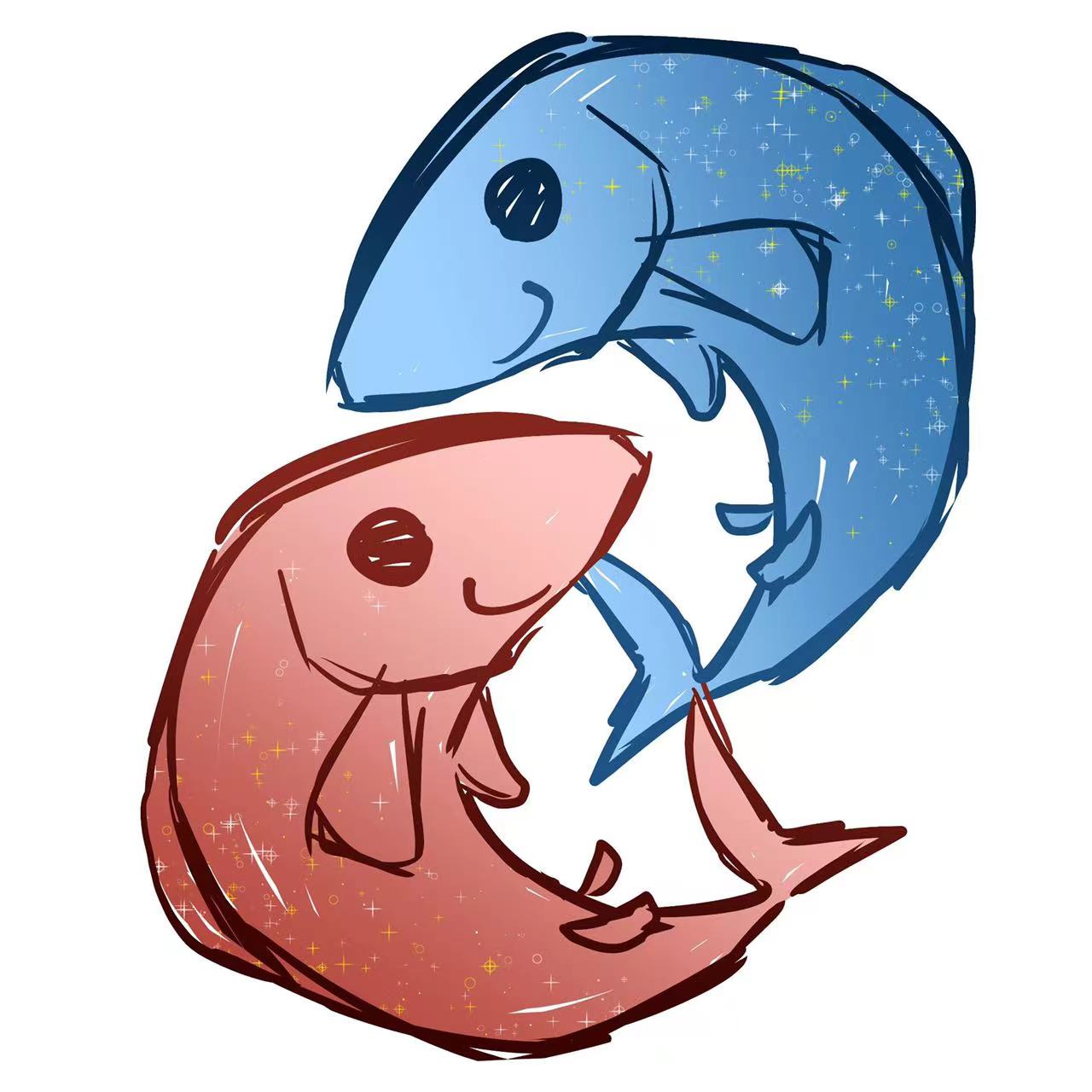Fri Aug 02 2024 00:00:00 GMT+0000 (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)
时间来到了早晨6点25分。
收紧了薄被,当我意识到我躺在床上的时候,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就高兴起来。
我试着去回忆,去捕捉那些稀疏的碎片。慢慢去拼凑,逐渐有了模糊的轮廓,随后又延伸了细节。当整幅场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时候,我很幸现在躺在床上,身上还有层薄被。
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虽然还保留着梦中的印象,却不愿再次回忆起来,每次想起都会有些后怕,又会滋生出庆幸。
时间还算比较早,这时的天还泛着一层朦胧的白,未曾被光完全刺破。
我拿起手机,想给我妈打个电话了。
响了半分钟,没有人接听,我把手机轻轻放下,眯起了眼睛。虽然醒来了,困意还没有完全退去,想多休息一会再起床。
另一方面,天虽算早,但我想我妈应该起床了,一般起床很早的。一会看到了手机,会给我回电话,所以眯起眼,也在等待手机的再次响起。
不一会,电话响了
“咋啦,怎么这么早打电话了“
”没事,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“
”院子里,树根长起来了,把地板都翘起来了,都不好走路了,我掀起来,把树根去掉重铺一下,刚刚在院子里忙着“
我想起了院子里的那棵树,这棵树跟我没有太多交集,我工作后,我们搬来了这个院子,这棵树才出现在我的世界中,没有我小时候攀爬的回忆,所以我的印象很模糊,只是隐约记得有棵树,有时候我甚至都想不起院子里有这棵树,只记得有另外一棵无花果树。
这棵树倒也不是很纤细,主干很粗,足足有半米的直径,枝繁叶茂,或许夏天也给了院落足够的阴凉。只是这棵树坐落的很隐蔽,位于门后墙体和前邻居的后墙之中,2/3的身躯都被墙体遮挡了,所以进门后,如果不仔细观量,可能就会忽视它的存在。
前段时间,规定说院落里不能有大树,所以它被砍伐了。
“那棵树不都被砍了,怎么还有根系”,回忆片刻,我对我妈说
“只砍了主干,根没完全去除,又长出了,这不,把院子里都整的乱乱糟糟的”
“娘,我爸昨天有没有给你打电话,昨天他生日嘞”
“没有,他不给我打,我也懒得打给他,打电话就吵架”
“哪里,哪里,前段时间你过生日,我爸不还买了好多东西”
“他哪是给我买东西,他是想让我去拿快递,顺带给我买了东西,你爸聪明着嘞,我给他说了,不要乱买东西,他都不听,他再买,我就不给他去取了”(村落里快递不能直接到家,一般都放到乡镇,所以取快递,都需要去乡镇取)
哈哈哈,我知道,两人都在刀子嘴豆腐心,“不管咋地,东西是买到手上了”
“娘,二涛说:最近咱们那有流感了,你要多注意,吃饭也得注意一点”
“二嫂,你哪个二嫂呀,我注意得很嘞,最近没啥活,天天在家呆着呢”
“二涛啦,不是二嫂。”
“哦哦哦,你在那也注意点,你跟你爸说没”(豆腐心)
“没有,我没听说他那有啥事,再说,他那边,院里人也多,没啥事”
“哦哦哦,那就好”
“娘,我一会起床洗漱啦,一会要去上班,先不多说啦,挂啦”
“好好好,挂吧”
此时,我体会到的是失落,是母亲的失落。每次打电话就像是一次短暂的狂欢,都不能称为短暂,如果每次假期相聚是短暂,对比这更像是稍纵即逝。对比这狂欢,我体会到的是更加悠远的失落。可是换个思路,失落中的期盼又给人慰藉着,就像是,假期回家前几日,母亲的期盼并不比相聚时相差很多。将时间延长,失落中或许也并不全是伤心,也会有期盼。心情似乎又好了很多。
时间七点一刻,我套上短裤下了床。领着花花下了楼。
出了单元,天气还算凉爽,有小雨滴淅淅沥沥的落着,这是我喜欢的天气。在燥热的赤夏中,这天气像一杯冷饮,那么的令人神往。心里有一句话,如果你想看看忙碌的人,就早起吧。这个时刻,世界在缓慢的恢复着秩序,小区保洁阿姨已经清扫了一半的楼层,道路两旁的汽车也在陆续的鸣笛,像奔赴战场前吹起的号角,又像是抱怨一天劳苦开始而嘟囔的牢骚,至于何种心情,全凭听者之心,目前来看,我的心情在这淅沥小雨中还是不错的。
回到家中,想起昨天晚上小区停水了,一整晚都在抢修,末了,还是没有赶上疲惫人们的困意,到睡觉时依旧没有到来。于是我走到洗漱间打开了水龙头,水呼啸而出,被关了一夜禁闭首次释放的张狂感,释放的又单单何止水,被夏夜浸泡的我们也需要释放。